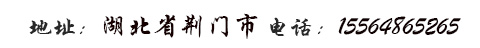金榜题名全国报纸副刊散文一览无余2
|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作者刘党英散文《母亲的鼾声》 ★检察日报绿海副刊发表作者沈顺英散文《雨润樱桃红》 ★大河健康报作品副刊发表作者潘新日散文《田生百谷》 ★商丘日报梁苑副刊发表作者陈玉岭散文《茶事》 ★南阳晚报星光副刊发表作者王树涛散文《约会》 ★天中晚报百姓写手发表作者刘久锋散文《北湖东园》 ★平顶山晚报副刊发表作者李人庆散文《长在泥土上的乡愁》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发表作者臧培育散文《那条野生鱼》 ★辽沈晚报迟桂花副刊发表作者唐池子散文《水杉长出了深翠色的眼睫毛》 ★焦作日报山阳城副刊发表作者廉彩红散文《蔷薇满城香》 ★周口晚报铁水牛副刊发表作者董雪丹散文《铁海棠:刺是锋芒,花是温婉》 董雪丹/铁海棠:刺是锋芒,花是温婉(散文) 友人送来一小盆铁海棠,一开始,在众多的盆花之中,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特别。后来呢,它红色的小花朵不停地、重复地提醒我注意它。 它到我办公室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停止过开花。茎的每一个分枝顶端,几乎都会抽出一个或两个长长的花柄,柄顶是朵小红花。花朵小小的,花瓣对错着。 铁海棠开花非常有趣:花中可连续开花,看上去就是一两朵花从下面的花芯中穿越而过,这样几个花朵的叠加,就形成一种很神奇的状态——花中之花。怪不得形容一个人喜悦时,可以说高兴得心里开出花儿来。 铁海棠还有一个让我喜欢的理由:即便花朵干枯,如果不去碰,它自己不会落下来,颜色也一直保持着很鲜艳的状态。 据说,铁海棠的花期,一般3~4个月,最长可达6个月。我这一小盆终年开花不绝,经久不谢,可能是因为办公室朝阳和光照温度都很适宜吧。 感觉疲惫,从电脑前站起来放松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观察铁海棠。 清晰地看到花时,常常模糊了它茎上的刺。 清晰地看到刺时,又常常模糊了它顶端的花。 尤其是拿起手机对着铁海棠拍照时,更是这种感觉。 它的花有着海棠的娇柔和明媚,它的茎又有着铁的冷硬和刺的固执。 它还叫虎刺梅,既有虎虎的刺,还有美美的梅。 它就这样将温柔与倔强、儒雅与刚烈、娇媚与决绝自自然然地融为一体。 看它时,可以因为一根刺而忽略它的全部花朵,就像可以因为一件可以抱怨的事而对整个生活不满,也可以因为它的花而忽略它的刺。而其实呢,眼前的美好在,刺也实实地在。 既然喜欢它的花儿,那就接受它的刺吧。当然,为花所动,还要不为刺所伤。 许多开出美丽花儿的植物都有毒或者有刺,它们应该无意去伤害谁,只是自我保护吧! 铁海棠,透过名中坚硬的“铁”,还是可以看到它心花怒放的柔软;掠过枝上的刺,还是可以看到它骨子里的温婉。 ★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作者刘心武散文《於梨华的悬空书房》 ★亳州晚报花戏楼副刊发表作者李丹崖散文《你吃过蒲公英吗》 ★邢台日报百泉副刊发表作者简爱散文《捉蚊子》 ★牛城晚报牛尾河副刊发表作者木文散文《向阳而居》 ★邵阳晚报神滩晚读发表作者江初昕散文《搭牢菜架挂果蔬》 ★天津日报满庭芳副刊发表作者张峻屹散文《记忆中的碾子磨》 ★重庆日报农村版副刊发表作者杨小霜散文《枇杷膏》 ★湖南日报湘韵副刊发表作者宋建民散文《桃源的街》 ★西安晚报文化·专栏发表作者杨海蒂散文《高原之上,雪山之下》 ★南阳晚报星光副刊发表作者尤红梅散文《忽而今夏》 尤红梅/忽而今夏(散文) 阳光正好,岁月静好,生活安好。 当大地的眸子开始渐次明亮,缤纷的鲜花开始装扮温柔的大地,鹅黄的叶子泛出满目苍翠,太阳悄然恢复久违的热情,我们不由轻轻感叹:忽而已入夏。 触手可及的绿色是夏天的主色调,随风飘舞的柳条儿在柔和的风中荡着欢快的秋千,哗啦啦地笑弯了腰。阳光无私地洒满人间,一树的墨绿尽情展示着它迷人的神韵。揪着一片绿叶凝视,叶脉清楚,树叶凝翠,呈上的都是绿的眉眼。放到鼻尖深深地一嗅,一股清香带着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微风拂过,树叶温柔地轻舞,倾诉对阳光的情意。那边的草坪早已铺成了绿油油的地毯,一群小孩在上面滚来滚去,笑声冲破了云天。油绿的小草张开火热的胸怀迎接人们,满地的翠绿让人忍不住想摸摸、坐坐,光着脚在上面踩踩,真接地气儿呀!前路多翠色,凝然绿欲滴。绿波荡日影,绿海摇夏风。公园里人们三三两两地奔走,休闲而惬意;几位老人唱起了《穆桂英挂帅》,投入而忘情;一群小孩正在画画,忙碌而专注。阳光正好,岁月静好,生活安好。伴一朵闲云,拈一片绿叶,拾一地阳光,让那些生活中或浓或淡的忧伤都随风而去。 五彩缤纷的花展示了浅夏梦幻般的魅力。月季花绽放得惊艳,绚丽了多情的人间。高处的花霸气地向阳怒放,中间的也恣情地舒眉展颜,下边的花同样千娇百媚。一棵树上开出了几种颜色的花,红的像晚霞在燃烧,灼灼其华;白的像雪片在飞舞,碎玉琼枝。花团团簇簇开放成彩墙,各色的花朵在绿壁上欢笑,迎接着络绎不绝的人流。娇羞的白玉兰比不上浓情的月季,在街角默默地绽放,火红的石榴把一个个小喇叭挂在石榴树上咧开嘴微笑,连路边的野花也忍不住来赶赴这场盛大的花事。谁持画笔当空舞?姹紫嫣红满画屏!此情此景怎不叫人陶醉?看不够,美醉了,摆出各种姿势,用手机把我们和花儿的约会留下,保存在相册里,珍藏在记忆里。 清晨像沉静的少女,碧空如洗,白云片片,丝丝清凉中夹杂着花香,让早起的人们在她的柔情中沉醉。傍晚像醉酒的汉子,传说中的火烧云在浅夏的傍晚隆重登场,漫天都是热烈的红晕。乡村在暮色中展示瑰丽的奇景,晚风轻轻吹过麦浪,浅黄的麦田涌动着阵阵波浪,与醉人的夕阳一同汇集在目光所及的地平线。彩霞满天,风吹麦浪,儿时麦收的记忆被忽然唤醒,一段岁月的碎片在回忆里起起伏伏。 大地凝翠,花开成海。浅夏,就是一首前奏舒缓而高潮热烈的老歌,在心灵深处欢快地奔流。 ★兰州日报兰山副刊发表作者张立新散文《牡丹成林香四野》 ★深圳商报万象副刊发表作者林国卿散文《初见百纳壶》 ★南通日报广玉兰副刊发表作者安铁生散文《木头人》 ★江海晚报夜明珠副刊发表作者刘伯毅散文《亲近茶》 ★安庆晚报月光城副刊发表作者董改正散文《腌笃鲜》 ★光明日报大观副刊发表作者王溱散文《满树槐花飘香来》 ★银川晚报凤凰副刊发表作者惠军明散文《五月里来摘樱桃》 ★贵阳日报作品悦读发表作者晓月散文《读书人的书卷气》 ★学习时报学习文苑发表作者朱广联散文《俭德萦怀好为官》 ★镇江日报芙蓉楼副刊发表作者王春鸣散文《他从七岁来》 ★大足日报巴蜀副刊发表作者赖扬明散文《痛的时候叫声妈》 赖扬明/痛的时候叫声妈(散文) “妈,痛!”李娟捂着被铅笔刀划破的口子,向妈妈哭诉着。 妈妈,取下眼镜,放下针线,凑过来,翻看了下李娟手掌。用嘴向伤口轻轻地吹风,并安慰道:“不痛了,不痛了。” 几声“不痛了”,好像是镇痛药,真不痛了。李娟默默地注视着妈妈,很想扑上去,凑近耳边说声谢谢。不料,妈妈却挥了挥手,招呼她:“继续做作业。” 日子是最好的创可贴,母爱是最好的烫伤药。 一日,李娟在取开水时,不小心将开水倒在了脚背上。李娟捂着脚,大声地哭嚷:“妈,好痛!” 一声“好痛”,叫得妈妈眼角的泪水犹如泉涌,一下子冒出来。她打来一桶冷水,边将李娟的脚浸入冷水,边向桶里吹风,边安慰道:“不痛了,不痛了。” 看着满眼泪花的妈妈,李娟擦干自己的眼睛。她想把妈妈抱紧,而后在妈妈的脸上亲吻一下,说声谢谢。可,妈妈站起来,走进卧室,去翻找烫伤药。她转过身去,擦拭了下眼眶。 一次又一次欲说的谢谢,都被卡在了嗓门,咽回心里。李娟总觉得自己亏欠母亲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和一声谢谢,而是一生都无法回报的爱。 爱是会传递的,从外婆开始。记得又一次,母亲外出活动,扭伤了腿,外婆得知后,比谁都急。看着肿胀的腿,外婆垫在手里,用嘴轻轻地向受伤处吹着风,并心痛地说:“不痛了,不痛了。”妈妈嘿嘿一笑,回敬她的母亲说:“妈,看您说的,把我当三岁的小孩了。” “有妈在,你都还是孩子。痛的时候,叫声妈!”外婆边说,边用那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手拍打着母亲的手。那一刻,母亲眼含着泪水,很想把妈妈抱在怀里,说上一声谢谢。可,外婆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去抽屉中寻找跌打止痛药。她侧身的片刻,眼角分明闪着泪花。 这一幕,总是那么熟悉,又总是那么给人无限感动和温暖。 痛的时候叫声妈,外婆说是她的口头禅,没想到妈妈也用上,且代代相传。 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就像是一剂良药,治愈伤痛的同时,又滋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随着时光远去,李娟成家立业了,也有了自己的女儿。 当女儿溜冰时候,不小心撞到了鼻梁。女儿娇声地哭到:“妈妈,好痛!”李娟边向鼻梁处吹着风,边安慰道:“不痛了,不痛了。” 女儿穿好溜冰鞋,转身而去,说了声“谢谢”。那一刻,李娟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冲着女儿嚷道:“团团,痛的时候叫声妈!”她静静地坐在木凳上,心里想:原来,每一个妈妈都一样,都有一句自己的口头禅。 “妈妈,好痛。”女儿过来,向妈妈撒着娇。 ★重庆晚报夜雨副刊发表作者杨恩芳散文《久违的童音》 ★如皋日报水绘园副刊发表作者宋继高散文《枇杷熟了》 ★今晚报今晚副刊发表作者周国平散文《疫情下对灾难的哲学思考》 ★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发表作者张小圈散文《桐花万里》 ★中国纪检监察报文苑副刊发表作者陈利生散文《炊烟袅袅》 ★桂林日报花桥副刊发表作者黄明海散文《散步桂林》 ★潮州日报今日闲情发表作者李良旭散文《三块木头》 ★滕州日报荆泉副刊发表作者韩云冲散文《黄台之瓜与李泌》 ★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发表作者王开散文《秋风长出了眼睛》 ★焦作晚报覃怀月副刊发表作者贾峰远散文《湖南情》 ★京九晚报夕阳红副刊发表作者王甫海散文《流淌不息的河》 王甫海/流淌不息的河(散文) 人到暮年,怀旧的心情就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一样,不时泛起阵阵涟漪,童年趣事如同电视连续剧一样,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这种情结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强烈。我虽然在退休后游览了祖国的许多名山大川,但是,我魂牵梦萦的还是儿时村后的那条流淌不息的小河。 春天,万物复苏,草长莺飞,大地渐渐睁开沉睡的眼睛,慢慢披上嫩绿的外衣。村后的小河总是在第一时间展露春的喜悦,潺潺流动的河水清澈见底,清风徐来,泛起层层涟漪。小鱼在水中游动,瞬间钻入水草丛中。河岸上的小草竞相破土发芽,近看却是刚刚拱出地面的草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小河两旁的梨树蓓蕾初露,大有瑞雪降临的征兆。 暮春时分,数以万计的小蝌蚪摆脱卵的束缚,争先恐后地在河里游动。这时,我和小伙伴们挽起裤腿在水浅的地方追赶摆动着尾巴的蝌蚪。我们有的用手捧,有的用草篮子捞,结果手捧时还是让蝌蚪溜掉了,篮子里的几个蝌蚪被捉住了。特别是盛夏,河水暴涨,水流湍急,蝉鸣、蛙噪和水声混成一曲高亢的交响乐,演奏得让人心情激荡。 炎炎烈日,酷热难耐,在烈日下锄禾的人们放下锄头,来到小河旁的梧桐树下纳凉,怡然自得。这时,小伙伴们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来到河边,毫无顾忌地脱掉裤头,一头钻入河里,有的洗澡嬉戏,有的抓鱼摸虾,开心的笑声荡漾在河面上,吓得青蛙远远躲在水草与荷叶下,不敢动弹。 在小河里洗澡的日子过得很快,河水一天天变凉,下河洗澡的次数也渐渐减少。一眨眼进入秋收时节,地里的谷穗儿弯了,高粱红了,棉花白了,黄豆荚咧嘴笑了……爹娘都在田地里挥舞着镰刀割谷子,举着抓钩刨红薯,我和小伙伴们就利用放学或星期天的时间偷偷聚在一起,悄悄跑到河堤两旁的红薯地里扒红薯。霜降后,凡是大红薯都在土里裸露着上半部,用手一提就出来了。每当晚饭时分,夕阳西下,我们趁大人们不留意,悄悄聚一起,有挖灶坑的,有捡柴草的,有扒红薯的,还有骑到树杈上站岗放哨的,不一会儿,河堤上就升起烧红薯的袅袅炊烟。 烧红薯时,我们根据风向,烧火的人要坐在灶坑也叫红薯窑的上风头,这样既能借风吹旺火势,也不会被炊烟熏呛,这都是从大人们那里学到的本领。先把红薯摆放在上面,下面用火把窑腔烧烫,然后把红薯推入窑肚内,上面用土封实,这叫闷窑。大约20分钟后就可扒出红薯开吃了。我们烧的红薯特别香甜,那个滋味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流口水呢! 我们不仅烧红薯,有时也烧毛豆角和鲜花生。由于红薯是柴火烧的,皮特别黑,剥红薯皮时手上被弄得黑乎乎的,吃的时候嘴巴上、脸上也被抹成了“黑老包”,像是长了黑胡子。吃完烧红薯,脸也黑了,手也脏了,为了回家时不让爹娘发现,我们干脆挽起裤腿,一字排开,站在浅水里洗手洗脸。清澈的河水没有一点污染,凉丝丝的,恬静惬意。这时,一抹晚霞出现在西边天际,我们这些吃饱了烧红薯、洗净了手脸、填平了窑坑的小伙伴们哼着儿歌,追逐打闹着奔向回家的小路…… 时光流逝。我童年记忆里那条潺潺流淌的小河啊,你在哪里?你那清澈见底、鱼虾游动、在蓝天白云下的身影怎么看不到了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歌声在耳边回荡,我仿佛就看到了那条潺潺流水、在蓝天白云下缓缓去向远方的小河……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cimeia.com/hcmyz/9556.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手养花,建议养这9种,好养活开花多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