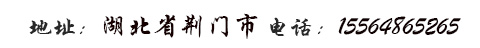迟子建伪满洲国
|
4 王小二在傍晚时总到松花江边逛上一圈。他来哈尔滨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一段雨水很盛,所以松花江水分外丰满。夕阳朝江水一侧沉沦的时刻非常有弹性,它探头探脑的,生怕落脚时风浪太大而闪了身子。当它终于被江水完全接纳之后,江面上就会涌动着柳叶形状的金光。王小二很喜欢看这些光,因为它们存在不了多久,把它想成什么就是什么。想成话语,它们就会发音;想成眼睛,它们就会眨来眨去;想成嘴唇,它们就会一张一合;而想成泪水时,王小二的眼睛就会花了,因为泪水像蝌蚪一样游进了眼眶。而这些想像的出处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吉来的姑姑,那个比他大出一轮的胖而爱笑的姑娘。王小二以为离她越远,会把她忘得更干净。谁料相思这种东西是愈远愈生动、缠绵和凄美。在制革厂工作的二姐见弟弟仍是孤身一人,就为他介绍女朋友。王小二看了两个,一个在孤儿院里当勤杂工,比他大六岁,又黄又瘦,胸是瘪的,可她却嫌王小二太单薄,怕他的身子骨将来经受不了摧打,婉言回绝了。气得王小二搓着脚直骂:“操,我还嫌她经不起摧打呢。”另一个倒是比王小二年轻,也丰满,腿粗得像刚灌好的香肠,一个嘴角有些歪,说是小时候有天晚上睡觉,未关好窗,邪风入内所致。她对王小二倒是一见钟情,所以接连三天往王小二的姐姐家跑,给他送热包子吃,还帮助王小二的姐姐洗衣裳。可王小二却看不惯她的歪嘴角,它好像永远对什么事情怀有不满,让人看了以为有什么事情对不起她了,王小二可不想在诚惶诚恐中过一辈子。所以为了报答姑娘对他的一片好心,他买了个花布兜送给她,做为友好的分手礼物。姑娘气得哭着把花布兜朝他怀里一扔:“留着你自己讨饭用吧。” 话是说到了王小二的痛处。他来哈尔滨后,还没有找到一份比较固定的工作,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使他顿生闲愁,所以每日黄昏都到江边去看落日。他觉得落日的命运比自己好,困倦之后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想睡在江里就朝江水深处落下,想睡在山里时就朝山谷落下。想必睡在江里的日子是想干净干净自身,而睡在山里的日子是为了沾染点花草树木的香气。有一两个捞鱼虾的人,他们撑着破旧的木船,在江上游来荡去,从他们近岸时麻木僵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收获微薄。 王小二一直把夕阳看进松花江里,看到金色的波光神灯般一盏一盏消失,这才朝家走去。 二姐家在道外北二道街,不远处就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制粉厂,王小二的姐夫就在那里磨面粉,所以每天回家一身的白。姐夫寡言少语,喜欢吸烟,牙齿黄得仿佛锈蚀了,因为胃不好,终 日打着嗳嗝,一股酸腐的气味在屋子里弥漫。二姐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五,一个十三,都很瘦,她们在上中学。十五岁的孩子叫谢子君,爱静。而十三的孩子谢子兰则爱说爱笑,喜欢唱歌跳舞,她每天傍晚都去道里石头街的一个俄罗斯老太太家中练习声乐。老太太是修筑中东铁路时随丈夫来到哈尔滨的,有一子一女。她丈夫去世后,她嫁给一位经营裘皮生意的中国商人。老太太精通古典音乐,她家有一架钢琴,她常常自弹自唱。谢子兰与老太太的孙女柳笆是好朋友,所以能够得天独厚地得到老人的指点。一旦谢子兰事先说要回来得晚,二姐就会打发王小二去接她。王小二基本不坐电车去道里,一是不喜欢电车在钢轨上行走 的“咣啷”声和牵引着电车的高空线所磨擦出的电火花,二是不舍得花那份车钱。由道外向道里的路很远,可王小二乐意行走。沿街会看到许多事情,譬如野鸡在昏暗的路灯下向往来的男人软绵绵地打招呼,譬如嗜赌成性的男人拿着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当铺换现钱,他的女人扯着他的衣袖哭嚎。还有披着水泥纸袋的乞讨者在菜市场门口捡那些已经烂成泥的蔬菜。当然也有一些有名的饭店在夜色中散发出柔和而富丽的灯影,诱人的香气勾人魂魄地飘扬出来;歌舞厅的霓虹灯变幻莫测地闪烁着。在这街上还能看到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的身影就像幽灵一样,使他们经过的街道有了某种神秘感。 俄罗斯老太太住在一幢米色的二层小楼里,大约有七八户人家,楼下的院子种着绿草和丁香,绿地倒是很干净,不过丁香树上吊着一些纸鹞,想必是淘气的小孩子所为吧。王小二见过柳 笆,她总是穿着白色的布拉吉,看人时笑意盈盈。柳笆的父亲是俄罗斯血统,而母亲则是中国人,所以混血的柳笆被人称为“二毛子”,她的脸部轮廓是西方式的高鼻深目,而身材和气质又具有东方的纤柔和典雅。如果王小二来得早,谢子兰还没有出来,他就坐在门前的绿草上望夜景,欣赏着从楼里飞出的琴声和歌声。柳笆的歌声像雾,而谢子兰的则像清澈的流水。每回谢子兰从里面出来,看见了王小二,就会把手搭在他的肩头撒娇般地说:“只有好舅舅才会来接我。”柳笆每回送谢子兰出来,看见王小二,就会埋怨他为什么不进屋子?屋子里有茶和点心,王小二就连忙声称自己喜欢坐在草地上,喜欢听草地上虫子的叫声,柳 笆就笑。柳笆一家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每个礼拜日都要去教堂做祈祷,在王小二看来,他们一家过的日子就像天堂般的生活。吃茶点、弹琴唱歌、做祈祷、去花店买玫瑰和百合,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穷人倒是也能去做祈祷,不过从教堂出来能够享受到的除了上天赐予所有人共同的阳光和空气之后,回到家里面临的还是黑黢黢的小屋里举步维艰的生计。所以王小二不信任何宗教,认为上帝或者其他神都是偏心眼儿。王小二的姐姐也信奉天主教,每回从教堂祈祷归来,她都显得无与伦比的平静和超然,在王小二看来,那也是一种麻木。只是不敢把这想法说出来,他倒不怕得罪上帝,上帝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怕姐姐伤 心。谢子兰其实有王小二那般高了,加上王小二长得比实际年龄小,所以他们看上去更像一对兄妹,谢子兰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感兴趣,表店、鞋店、饭店、时装店、冷饮店、花店,而王小二能陪她逛得起的,只有冷饮店。谢子兰一顿能吃下七八块冰糕,问她的胃能否消受得起,她就打着哆嗦连连点头,并且用舌尖去舔唇角的冰糕沫,说:“没问题!”王小二却没有这本事,两块冰糕落肚就足以让他打寒颤了。谢子兰便嘲笑舅舅身上没火力,要是上了战场非得当逃兵不可。王小二有些恼火,但一想自己算是长辈,就由谢子兰胡说,不过下回再进冷饮店时,他就说钱带得少,只能请她吃两块冰糕。谢子兰嘟一下嘴,很仔细地吃掉两块冰糕,然后对王小二说:“舅舅,我觉得你这个人内心是勇敢坚强的,你上了战场一定能当英雄!”王小二明知这是个温柔的陷阱,可还是不能自持地跳进去,他会装做无意地翻一下口袋,带着惊讶的语气说:“噢,这里还有几个钱,够你再吃几块的!”谢子兰的嘴角便会泛上得意的笑容。他们吃过冰糕走出冷饮店后,谢子兰就会张罗着坐电车回家。她倚着车窗,看见大饭店门前进进出出的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就会有些失落地说:“有钱人过得可真舒服哇。” 王小二的姐夫见内弟只是吃闲饭,还占据了本来就不宽绰的家中的一间屋子,就有些不太痛快,时不时阴沉着脸,把咳嗽声搞得很响,好像向人家示威:他的气血已为维持这个家耗得差不多了。有时他还去装做无意地说他路过哪家厂子,见门口聚了好多人,都是去招工的。王小二就很知趣地问那厂子在哪,做什么活计,然后跑去碰运气。然而结果总是碰一鼻子灰回来,令他愁肠百结。他开始怀念在新京的生活,怀念王金堂、吉来和馆子里的那些伙计。在哈尔滨,他连个可以痛快淋漓开玩笑的人都没有。虽然说哈尔滨看上去很洋气,满街的欧式建筑,各类教堂晚祷的钟声不时响起,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某种庄重感,他对它还是喜欢不起来。相反,有些土气的新京倒给他一种温暖感。王小二想着如果到秋天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就打道回府,给老板娘陪个不是,继续当他的店小二去。然而未到天高云淡的时节, 王小二的命运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进入七月中旬以后,天气总是阴多睛少。老天仿佛有了极端悲痛的事情,三天两头就哭一场,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没了。松花江干流的水位突涨,以往平静的松花江突然变得狂躁起来,腾起的巨浪激烈地拍打着大江两岸的堤坝,江面凉风漫卷,给人一种鬼气森森的感觉,再没有人敢撑船去江里捞鱼虾了。八月一日,江北的小岛已是汪洋一片,江南市区的低洼之处,也已积水成潭。王小二姐姐家所居住的地方,江上是石坡土堤,堤上砌有防水墙;而过了道外十八道街,则一律是土堤。这些堤坝段面狭窄,多年失修,毫无防御能力。八月七日凌晨,大多数市民还在梦乡中的时候,道外九道街江堤首先决口,倏忽间就垮掉了五十多米,洪水咆哮着冲入市区。一些早起的小摊贩正准备在街角支起摊子卖早点,忽然间被滚滚而来的洪水给吓得懵头转向。 他们一时以为眼花了,洪水怎么可能说来就来了呢。然而洪水的的确确是上岸了,而且像一群雪青色的骏马一样膘肥体壮地穿街走巷,首先将几个不知所措的人掠倒。年轻力壮的人从水中爬起来了,而一个患风湿病的老人则彻底被它劫走了。王小二正梦回新京,领着吉来到城南的影剧院看戏,说是铃声响后就开演。可铃声叫了十几分钟,还不见银幕上有影子在动,王小二就愤怒地高喊:“开演了,到点了!”结果他把自己给喊醒了。他听见马路上一片喧闹,姐姐一家人也从梦中醒来了,谢子兰撩开他住屋的门帘惊慌失措地说:“舅舅,发大水了,快起来吧!”王小二的姐姐家在三楼,他朦朦胧胧挨近窗口,向下一望,了不得了,洪水已经切断了能望得见的一切道路,水泛着白沫拍打着房屋,人们大呼小叫着,不知该逃到哪里去。发大水不像着火,起了火人们只管离开现场就是。而水患则迫使人们往高岗上跑。可是外面已是洪水汹涌,又没有船可以游荡出去,于是绝大多数住户通过烟道或者天窗攀上屋顶。 王小二的姐姐跪在圣母玛丽亚的像前祈祷,口中念念有词,王小二便冲姐姐说:“那个胖娘们儿在天上,没有水淹得了她。她不会管你的,求她有什么用!”他把圣母玛丽亚称为胖娘们儿,惹得危难之中的谢家一对姊妹吃吃地笑起来。 姐姐温和而又是严厉地对王小二说:“还不快忏悔!” 王小二说:“她要是能把这洪水给立马退了,别说是忏悔,我认她当咱的干娘也成!” 姐弟二人在关键时刻为了玛丽亚而拌起了嘴,这使做姐姐的觉得弟弟罪孽深重,连忙又为弟弟祈祷,请求圣母宽宥弟弟的无知和莽撞。王小二见街道上仍然有人在水中打着晃扶着墙走路,便知水深不过两尺有余,便穿鞋下楼要去街上转转。谢子兰连忙拉住舅舅说:“你又没有船和救生圈,不能到街上去!”王小二笑嘻嘻地说:“我是鱼变成的,洪水吞不了我。”一直沉默不语的姐夫突然说:“面粉厂的面粉还不得全泡汤了?你要是不怕,就跟我去厂子搬面粉!”王小二答应着,就随姐夫下楼。谢子兰在他们背后带着哭音说:“咱们家的人都有毛病,顾别人的命不要自己的命!我得要自己的命!要是我死了,你们还到哪里听歌去!”说完,她满腔悲愤地怒吼了一声,随手把一只茶杯从窗口抛向窗外的洪水中。 除了道外区的江堤决口之外,没有几日,洪水又汹涌澎湃地涌入道里。它们犹如一条条飞舞的银蛇占据了繁华地段,把一群一群罹难的人赶上南岗的高岗。许多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文庙和极乐寺一带。极乐寺的僧人竟然随着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携带着猪羊祭品,驻足江岸燃放鞭炮,焚香诵经,祈求水神保佑。诵经声就像一群蚂蝗在飞,虽然洪水不能遏止它的存在,但诵经声同样也不能遏止洪水的存在,它一意孤行地深入市区,把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城。然而洪水终于玩厌了。它嚣张了几日,尽情抚摸了街道和一些教堂的建筑,觉得陆地的日子不过如此罢,于是就偃旗息鼓地退潮。市民们又纷纷回到自己的住屋。住在底楼的人家不得不在叹息声中翻晒那些被淹的物品。王小二的姐夫自水灾后对王小二另眼相看,因为他帮助自己谋到了一份好差事,在制粉厂看管仓库,不用再消耗体力,这完全赖于水灾之时,他能勇敢地带着内弟赶到厂里成为第一个抢救仓库面粉的工人,他为此还多得了一个月的薪俸。而王小二也在柳笆家找到了差事。这个差事来得很偶然。有天晚间他去接练唱的谢子兰,在院子的草坪上听见两个男人在为一笔大豆的账目的计算而颇费踌躇,善于心算的王小二听明白了他们计算的内容,就走过去把结果告诉给他们。其中有位就是柳笆的父亲阿寥沙。阿寥沙说你这么精明,在街上闲逛可惜了,跟着我做生意算了。王小二自此摇身一变,换上一身体面的服装,成了阿寥沙所办的粮油购销公司的一名职员。 5丰源当的招幌有两个,一个常挂,另一个则常歇着。常挂的招幌是长方形的木牌,四角用铜片包饰,上方“丰源”二字以小字号面目出现,而“当”字则大得如一块巨石,占据了招幌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使得“当”字上方的“丰源”二字更像落在大树梢上的一对鸟儿。另一个招幌是木制包铝的,青白色的,上面的字迹规模与常挂的招幌基本一致,这种招幌只是逢了雨雪天气才出,名为“雨牌”。别看雨牌出工的日子少,可它为当铺迎来红红火火的生意,许多来当东西的人纷纷打着雨伞,络绎不绝地朝丰源当来。被当的东西掖在怀里,而当东西的人则能把头埋在雨伞下,分不清他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雨伞就仿佛一块遮羞布,把当者的窘态完全掩埋住,他们的自尊仍能像炉中的残火一样得以维持。至于从当铺中典押出来的钱,他们就跟结核病人脸颊上的红晕一样,带给当者的只是一种虚假的丰盈。从丰源当出来的人,有的步态踉跄,有的则脚下生风。步态踉跄者多半是家境贫寒而又本性善良的人,他们去米店或者药铺买家里应急的东西。而脚下生风的人多半是去了酒馆、赌场或者妓院,在这些场所熬一夜出来的男人,不惟钱袋空了,步态也踉踉跄跄了,他们也一样家境贫寒,只是生性浪荡而已。 丰源当算不得奉天的名当铺。它并不位于繁华的市中心,所以远离一种喧闹。但它也并不偏僻,周围既有茶坊也有戏院,不远处的烟馆也招徕着南来北往的客,这使得它的生意一直没有过分冷清过。 王恩浩一直觉得丰源当的格局极像父亲的罗锅形态,看上去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当铺的门脸比较简陋和狭窄,看上去只是临街的一座青砖瓦房,招幌挂在探出屋檐的一根铁质横梁上。而它的背部则内容丰富得多,给人一种富贵人家后花园的感觉,幽深而奇丽。后部不再是平房,而是依着平房而起的一座三层小阁楼,被典押的物品都存放在这里。一层主要保管着所当进来的比较廉价的物品,多为普通的衣服和简单的生活日用品。在它的西北角有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更房,是守夜人的居所,一根被磨得极为光亮的松木柱子上挂着盏马灯。二层为稍为值钱一些的物品,如裘皮和古董。这里最主要的是防虫和防晒。裘皮怕虫咬,而古董惧骄阳暴晒。三层为首饰间,无数的红色织锦盒大大小小地摆在木格架上,里面装着珍珠、玛瑙、玉石等等材料做成的戒指、项链、手镯、头簪和耳环,让人觉得这是女人的天堂。 防火墙从一层一直穿越至三层,通风口每层皆有,而窗口的设置则是各层有各层的不同。一层窗口很多,二层居中,三层最少,只有两个,好像是首饰间不需要阳光。也的确,那些珍珠、玛瑙的光泽已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了,虽然说它们被封闭在织锦盒中,但任何走入首饰间的人,都会觉得有一种别致的光芒在房间游荡。一层正门的左右两侧供奉着火神和号神;库房忌火,便以火神为尊;又忌耗子肆虐,便尊号神。此外,丰源当大柜台的正北方向的神龛里还供奉着“三财”,即赵公元帅、关夫子和增福财神,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为“三财”上香。丰源当的历史不长,只有七年。它的主人王恩浩刚满四十,体魄健壮,面目白净,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像是一尊佛。他走路慢慢腾腾,说话慢条斯理,看人时目光也是慢慢的,所以经常引起一些女人的幻想,把王恩浩慢慢的目光理解为一种痴情。有意于他的女人就卖弄风情或者暗送秋波,结果都是失意而归。暗送秋波的女人兀自长叹一声了事,而卖弄风情的女人自认是绝代佳人,便忍不住怒气冲天地骂他:“瞧他那副德行!手指比女人的还长,走路慢得像女人揣了崽子,胡子稀得就要望不见,那裆里的玩意肯定是软的!”当然,骂也是骂在了背后,王恩浩听不见。听见的人赵钱孙李都各不相同,大家也是笑笑而已。王恩浩依然走他的慢步,用他女人般的纤纤长指拈起围棋与人对弈,而且常常在入夜时分去当铺去看那些有沧桑感的物品,在昏暗的灯影下,陷入无边的遐想之中。 丰源当的人对王恩浩都很尊敬。他从不对人大发脾气,也不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逢年过节,他还多为当铺的伙计发一些钱,所以闻讯而来找事做的人很多。王恩浩用不了那些人,只能 婉言谢绝。他用的人对典当业务非常精通,就是初始不太懂的人,慢慢也很精通了,他们觉得端王恩浩的饭碗要对得起他。有一年丰源当的头柜陆子宣收当了一只明代官窑的青瓷花瓶,在他转身的一瞬,被当者掉了包,将真品迅速收回,而将惟妙惟肖的赝品摆在原处。陆子宣浑然不觉将它收当入库。待到发现上当时,已悔之晚矣。陆子宣自觉对不起王恩浩,就将这笔令丰源当受蚀的钱补给王恩浩,打起行囊准备回家。王恩浩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陆子宣为此事回家后一病不起,撒手西去。王恩浩闻讯后,亲自前去吊孝,把他的丧葬费用全部包揽,并且让他的小儿子来当铺当学徒,给他口饭吃,一时成为丰源当的美谈。 王恩浩不穿皮鞋,喜欢布鞋,而且是那种看上去笨头笨脑的圆口布鞋。他的鞋是住在丽水巷的张荣彩老人专为他做的。她是个七十多岁的孤老太婆,喜欢做鞋。她的炕头上总是晾着袼褙,雪白的麻绳一团团堆在柜顶。别看她年纪大了,纳鞋底时用锥子依然有力气,一锥子就扎透,将麻绳穿进去后一提一顿的动作也很利落干练。她做的鞋子耐磨而舒适,所以生意也不错。她基本上是为老主顾服务,将吃喝钱赚足后,她就会歇息几天。她到街上喝茶、吃酸菜水饺,也去邻居家嗑葵花籽谈天说地。人家见她七十多岁还有一口白牙,眼睛也不花,就说:“你活一百岁肯定不成问题。”她就一撇嘴说:“这世道有什么意思,我活够了。”人家就问她:“这世道怎么了?”她就一捶腿说:“咱们祖宗留下的地让小日本来住了,真不像话。”说完,眼神就凄凉了。别人也觉着凄凉,大家就不多说了。张荣彩老人的老伴去世得早,儿子在南京教书,几次来接她去,她嫌南京是个火炉子,自己身上没有多少油让它煎熬了,说什么也不去。在做鞋的老主顾中,她最喜欢王恩浩,认为他是个菩萨心肠的人,常常唤他为“干儿”。王恩浩也唤她做“干娘”,每次取新鞋时都要带些点心水果给她,她总是劝王恩浩把丢在外地的妻儿老小接来。“一家人不在一个地方过日子,那还叫一家人嘛!”她这样教训王恩浩。她知道王恩浩月月往家中寄钱,在她看来,既然有钱养老婆,就要把老婆 放在身边才对头。不过王恩浩依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这使老人大为不满,声言不再给他做鞋穿了。但他一见着王恩浩,心就软了,觉得干儿子不像是那种负心的公子哥,他在奉天也从不拈花惹草,想着也许他是男人当中的格路人,也就不再教训他。不过最近老人对王恩浩经常出入大和饭店大为光火,她认为去那里吃日本饭就是对祖宗的不敬,并且认定他还睡了日本女人,不然怎么一连两个月不登她的门了呢!“他一准是套上了狼,不穿布鞋了!”老人这样对自己说。她认为皮鞋不是人穿的东西,跟石头一样板脚,所以把它称为凶恶的狼。若是她看见老熟人中有穿皮鞋的,就撇着嘴角十分小孩子气地说:“套着个狼不咬脚哇?” 人家为了逗她,就说:“不咬脚,挺舒服的。”她就气得直喘粗气,并且大声宣称阎王殿里不收那些穿着皮鞋的人,让他们下一世没有去处,孤魂像野狗一样游荡。人家依然笑着说:“那才好呢,阎王殿不留人,就永远留在人世间!”老人便无下文了,只能干咳几声,捶捶腰,慢悠悠回她的屋子继续纳鞋底,边纳边唱乡间俚曲,不亦乐乎。王恩浩最近每个周末去大和饭店,是因为认识了山口川雄。山口川雄行伍出身,来到中国后本应在军中服役,然而不幸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就由在奉天经营满铁的舅舅给安排在一家外国银行工作。山口川雄喜欢古董和围棋,汉语讲得格外流利,对战争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与王恩浩一样喜欢沉 湎于旧物所营造的哀婉侈靡气氛中,所以他们一拍即合。他们相识在丰源当挂雨牌的一个黄昏,街巷中细雨敲击青瓦的声音分外缠绵,天色黯淡得使房屋的轮廓模糊不堪,王恩浩正在三层的首饰间看一只镶嵌珍珠和玛瑙的头簪,负责付赎的刘东贵上来向他请示,说有个人持了当票来赎杨玉井当的一只唐代鱼纹彩陶,声称是杨玉井的至交。期限和当票都合乎手续,只是来者不是杨玉井,怕是杨玉井不慎把当票丢了,让人给捡着了。如果物品被冒赎,当铺有损失不说,杨玉井那里也不好交待。王恩浩也觉得马虎不得,杨玉井前一段贩卖烟草失利,不得已才当了这只心爱的彩陶以解燃眉之急,若是杨玉井真的不慎丢了当票也该差人跟他 说一声才是。带着这份蹊跷,他随刘东贵下楼去察看取赎的人。 他从来者的相貌和语调中立即觉悟到他是日本人。山口川雄穿着件墨绿色雨衣,腰微微弯着,苍白的额角上有汗珠滚动,气质十分文弱。尽管他的汉语讲得比较地道,但从他语间的停顿和尾音处理的生硬来看,他并不是中国人。王恩浩看了当票又仔细询问了当票的来历,山口川雄说是喜欢中国的古玩,听说杨玉井那里有一只上好的唐代彩陶,于是就托人去找他,不料杨玉井把它当入丰源当了。山口川雄就说服了杨玉井,买来当票,又付了一大笔钱给他,日日盼着赎期临近的日子。王恩浩忍不住问他:“你又没见过这只彩陶,怎知真假,不怕上当?”山口川雄很认真地说:“人家都说丰源当信誉好,我想当进这里的东西都是被行家 验定了的,不会有假。”说完,他微微一笑。他笑的时候抿着嘴角,很矜持。王恩浩凭直觉判断不会有诈,就唤刘东贵付赎。山口川雄见到彩陶那一瞬间沉郁的眼神突然灼灼动人地亮起来,他抚摸彩陶的手指战战兢兢,极像一位生者在抚摸挚爱亲人的遗骨,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王恩浩就是在那个瞬间把他认定为自己的朋友。他唤人烧水沏茶,到后楼的居所与山口川雄饮茶对弈,仿佛与他相识已久。他们的棋风都很相似,温和而少见锋芒,又绝少出纰漏,所以一盘棋能下得很长,最后总是在胜负未定时推开棋盘,谁也不计较输赢。山口川雄谈日本的茶道、歌舞伎和插花艺术,而王恩浩则谈中国的山水画和古代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他们越谈越投机。从此之后,王恩浩与山口川雄常常聚会,有时在丰源当,有时去大和饭店。大和饭店位于火车站东北方向,在浪速街与富士见街的交叉口,看上去气派典雅。豪华的大餐厅的正面有舞台,在这经常有音乐会和舞会举行。出入大和饭店的多为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俄国人以及奉天各界上流阶层的人士:阔商、军官、领事馆的官员以及戏院当红的名角。王恩浩和山口川雄从不下舞场,只是吃饭喝茶,谈天说地。王恩浩很喜欢日本的清酒、米果和鱼丸,它们清淡的风味很对他的胃口。 从大和饭店出来,大多的时候夜色已深,他们叫来一辆车,穿越满城的灯火回家。多半的情况下是王恩浩送山口川雄先回去,他体质弱,王恩浩希望他能及早上床休息。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有两次王恩浩贪杯过甚,不胜酒力,刚被扶上人力车就呼呼大睡,山口川雄只能先送他回丰源当。丰源当值更的老头挑着盏昏蒙蒙的马灯迎在路口,看到主人醉得里倒歪斜的,只能叹着气把他扶回屋里。有次更夫有意无意地对山口川雄说:“我们家主人以前从不这样,他要是让人瞧不起了,我们也没脸面见人了。”说得山口川雄不敢再请王恩浩去大和饭店,有时只是从店里把王恩浩爱吃的几样东西买了来,租了车直接来丰源当。丰源当的人都知道山口川雄的真实身份,所以对他既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冷淡。太热情有些违心,而太冷淡又恐主人不快而砸了自己的饭碗。战乱中的饭碗无疑像树上的金苹果一样诱人。这样往来久了,王恩浩与山口川雄的友谊就与日俱增,一周不见就想得慌。他与山口川雄时常流连于当铺的古董柜前,爱不释手地把玩一件件或朴拙或精雕细刻的器皿,沉浸在对远古历史的追思之中,有时恍若听见了凝聚着膏脂的富丽的流水,水上漂浮着花瓣和夕阳,小桥一侧的茶坊就有琵琶声传来,烧制器皿的窑火像晚霞一样绚丽地弥漫。如果逢到外面有风或雨,他们的内心就有一种泪如雨下的感觉。 不过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王恩浩不喜欢女子和孩子,而山口川雄则在恋爱之中。王恩浩见过那个叫于小书的姑娘,她的圆脸粉嘟嘟的,看人时敛着目光,有些害羞又有些生怯的样子,分外惹人怜爱。山口川雄问王恩浩对自己的女朋友有何印象,王恩浩冲口而出:“还不错,穿着圆口布鞋,一看就是个好女孩。”说得山口川雄不由得大笑起来,并以此推断王恩浩只喜欢穿布鞋的女人。 王恩浩确实没有对任何女人动过心,尽管他娶妻生子,也曾过了一年多的婚姻生活。他与老婆只上了屈指可数的几回床,觉得男女之间赤裸裸的肉体交欢实在不雅,所以清晨起来穿上衣服后就有一种摆脱不掉的羞耻感。他的父亲王金堂一门心思地要抱孙子,见儿子时时抱着枕头去另外的屋子睡,就拿着木棍去打儿子的屁股,骂他是睡在土中的鼹鼠,灰头土脸不明事理。待到后来王金堂发现儿媳的肚子一天天蓬勃壮大起来,就不管儿子去哪里睡了。吉来满月刚过,王恩浩就离家出走了。走前他希望与老婆脱离婚姻关系,让她再去嫁个喜欢的人,女人哭着说:“只要你活着,我就是一辈子不和你住一块,也是你的老婆。我会帮你伺候老人和孩子。”听得王恩浩险些落下泪来。他到沈阳先是在一家钱庄当职员,后来靠与人合伙由江浙贩卖茶叶而发了笔财,盘下一块地皮,依着间老房子开起了丰源当。他偶尔也能想起老婆温顺隐忍的眼神,想起她浑圆的胳膊搂着他脖颈时的那股力量。想起他离家出走时只像个小肉球一样蜷在老婆怀里的儿子,然而这些想头就像树梢上的秋叶一样经不起吹打,些微的风雨就把它劫掠一空了。 张荣彩老人眼见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凉,王恩浩还没有来做棉鞋的意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有一日午睡起来,她喝了两杯清茶后就放开大脚朝丰源当走去。她不裹足,虽然遭到了同辈老女人的耻笑,可她在街巷中穿行时总是比她们首当其冲,步态稳健而快捷。她的老主顾见她一副风急风火的样子,都问:“这是去哪?”“丰源当。”她答。“看干儿去呀?”“哼,他眼里哪还有我这个干娘!”老人气咻咻地指着街上的树叶说:“都快黄了叶子了,连个影子都不往家里招,这个小王八犊子!” 丰源当的中缺开完一份当票正欲把它递给典当者的时候,一眼望见了张荣彩老人穿门而入。看来是路上走急了,她额前一绺花白的头发被汗水濡湿了,像团残雪一样显出很脏的样子,再加上她衣襟上满沾着打袼褙时弄上的糨糊,使她看上去颇有几分乞讨者的落魄相。中缺知道老人不缺钱用,不会是当东西来的,于是就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快歇歇脚吧,累了吧?”老人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把一口痰吐在里面,然后团成个球随手掷向门外。她用颇为理直气壮的口吻对中缺说:“把我干儿给揪出来,这个小老鼠藏到哪里去了,干娘来了也不见,真是越来越没王法了!” 王恩浩其时正换好衣裳准备出门,去估衣行处理几项死当,听见了干娘的声音,就满脸笑意地迎了过来。老人见干儿的胡子刮得雪亮,衣着也洁净,精神头十足,而且脚上仍然穿着布鞋,火气就撤了几分。但转而一想他过得好好的却不知道看望她,不满的情绪又潮涌般袭来。她也不顾周围有客人和丰源当的职员在场,指着王恩浩的鼻子说:“你跟我说说,你怎么跟个日本人好起来了?那大和饭店是咱们这路人去的地方吗?” 王恩浩的脸刷地红了,但他仍然殷勤地陪着笑脸,招唤干娘去他后院的屋子叙谈。老人便十分孩子气地说:“那你得给我沏上好的龙井才是!”王恩浩连连点头。老人又颐指气使地说:“还得给我备一盘刚出炉的红豆沙馅饼。”王恩浩连忙回头吩咐当铺的伙计:“快去买两斤刚出炉的红豆沙馅饼。” 老人走向后院的通道了,但她硬朗的声音仍然铿锵有力地传回收当的职员的耳朵里,她说:“你跟我说说,你是不是睡了日本娘们儿,你把自己的种子撒在别人的地里,会吃大亏的,知不知道?” 不知道王恩浩听了这话是什么心情,丰源当的人却是不约而同的笑起来,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开怀过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cimeia.com/hcmzz/8876.html
- 上一篇文章: 两会提出残联下达残疾人证身份证你真的了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